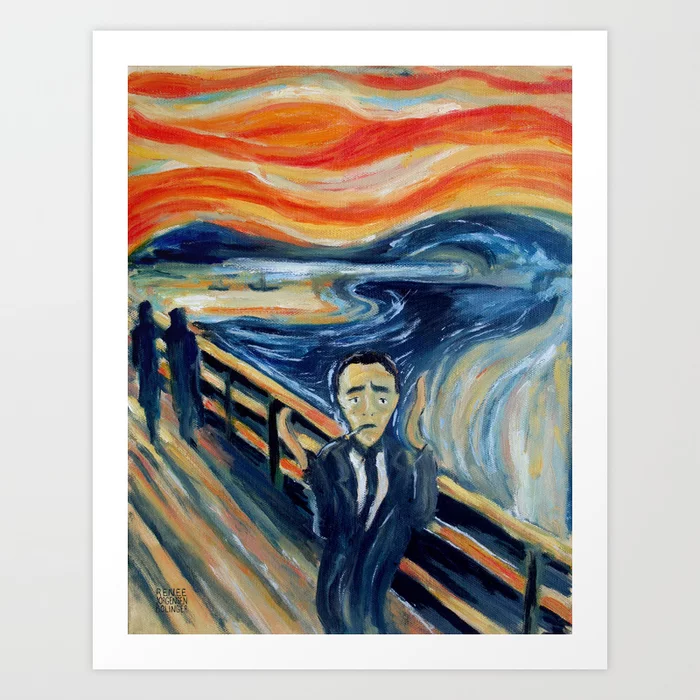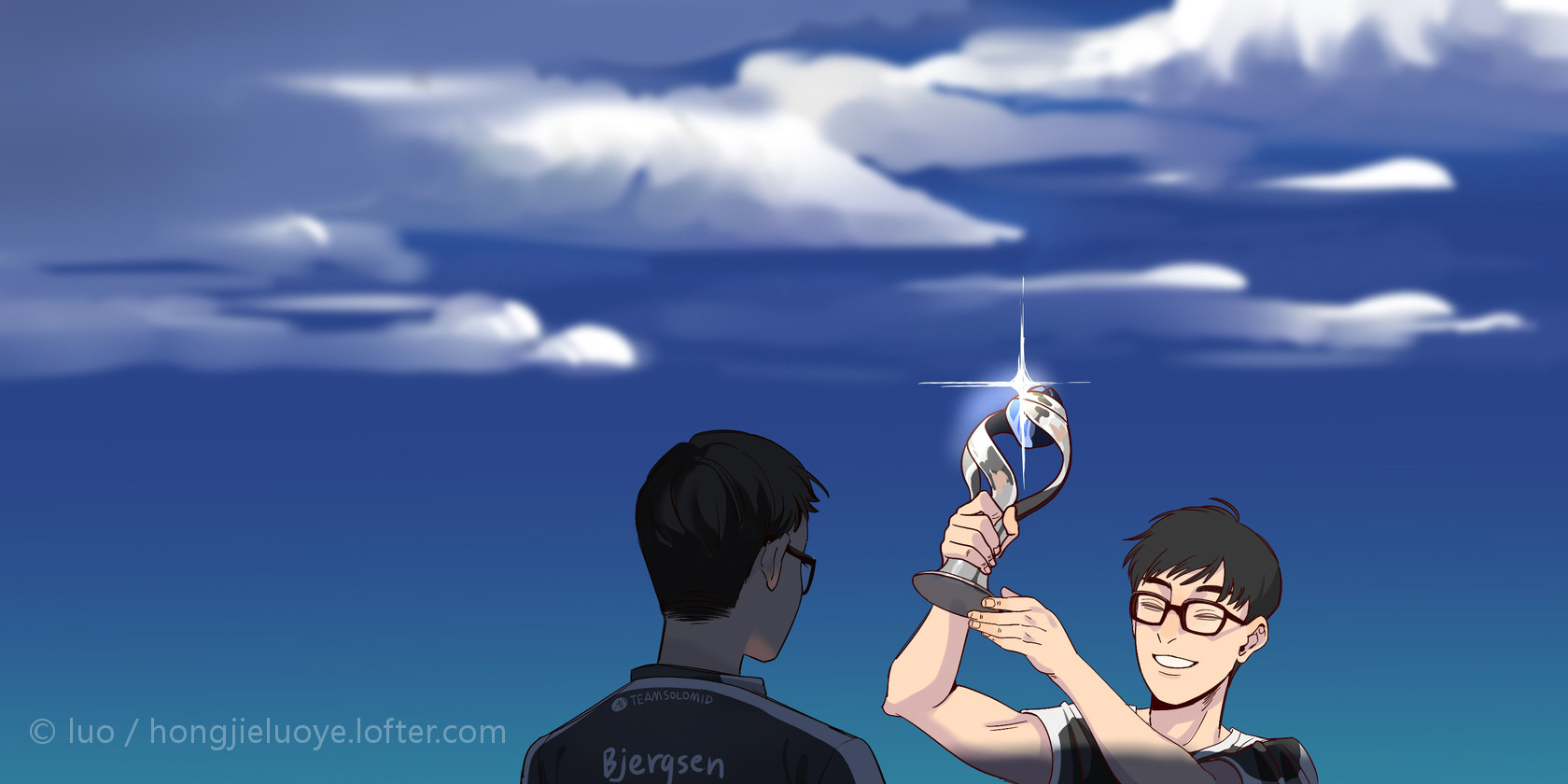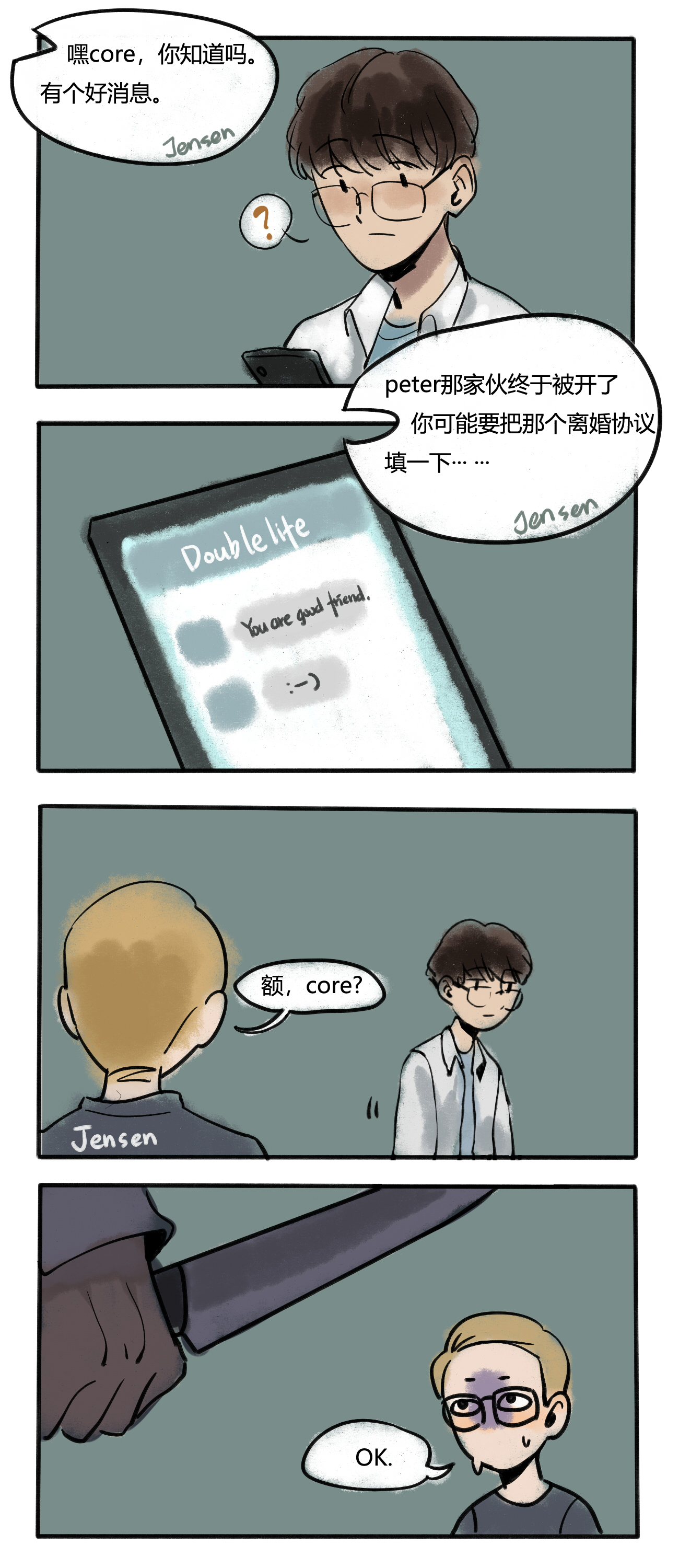随笔 · 当我在写同人的时候我在写些什么
2011年我在百度贴吧上写下第一个长篇故事,女主角是一个金发的女剑客,我在课本的封皮上画了好几张堪比火柴人的插图,放在今天,它大概应该被划分到乙女玛丽苏这个分类里。
那二十万字在如今的我看来已然不堪回首,但那一年我母亲认认真真地读完了六十章充斥着“天上地下唯我独尊”风味的乙女文学,然后以一种赞叹的口吻说,写得真好。
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。
尽管我很想嘲笑自己在小学的时候写下的二十万字傻白甜文学,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它们是我再也无法写出的美好文字。
它折射出的是我无忧无虑,纯粹快乐的童年。
百度告诉我乙女文学是将自我代入角色的美好想象。但后来童年时的风筝飞上云端,消失不见,落下的是一张名为成熟的罗网,每长大一岁,就勒死一颗天真的幻想。
童年结束之后的每一年,我都会在某个筋疲力尽的夜晚问,“明年我可以休息吗?”
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
我十五岁的时候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另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,那一年我平均每天只睡六个小时,而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只能睡六小时的一天。
我在教室里从冬天坐到夏天,最热的时候手掌上汗渍黏黏地往薄薄的试卷上沾,握了很久的笔,被挤得扁扁的的指尖,磨得光滑的皮肤,至今在中指上残余下两个厚厚的笔茧。
有一天晚自习结束下了暴雨,我父亲来接我的时候没有带伞,于是他把车熄了火停在楼下,说我们在这等一等吧,雨停了再走。
南方夏天的雨很大,像瀑布一样泼在车窗上,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错觉。那时候我希望雨永远都不要停,我不用回家打开台灯,去学那些永远都学不完的算式,然后又在清晨五点半睁开眼睛,开始周而复始的明天。
好像在非常漫长的几年里,只在暴雨中的那十分钟,我真正感受到了来自少年时代的,鲜活的空气。
于是我闭上眼睛,想象故事里的高渐离和雪女盛着一条小舟扬帆南下,远离咸阳,远离兵车千乘的大秦。他们并肩抵足而眠,呼吸着银河洒下的星光。河岸两边的山脉是模糊的黑青色。然后山随平野尽,江入大荒流。他们独自漂到天涯海角,和世界上的所有人共同拥有头顶的月亮。
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这种想象中坠入梦乡,但我最终没能写完那个故事。
我坚持对自己连载这个故事直到高考前的最后一天晚上,然后大一的我很快忘记了高中的自己因何而流泪,于是故事也永远停在了一条逃向远方的船上。
“明年我可以休息吗?”
三年后我像条无家可归的狗一样在中关村苟活,五道口的黄昏总是会让我觉得自己渺小如尘埃。晚上九点的时候走回学校的路仿佛是一线微不足道的喘息,黑沉暮霭下的人流像泡在雾里的鲤鱼脊,偶尔有车灯的光在背着公文包的男人的侧影上流转,我觉得自己恰到好处地隐藏在其中,任凭微不足道的意识流淌。
我在心里恶毒地诅咒我的导师,诅咒所有让我感到痛苦的人,而后花十块钱在东源大厦的路口买一纸包裹着脆糖霜的小番茄,甜腻的汁水溅满口腔。它真的很好吃,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层甜甜的糖衣。
实验室的北京朋友对我说起小时候老胡同里的日子,说起她的姥姥会在过年的时候在四合院里铲雪。我递给她一个糖霜山楂,她说不够甜。
但我不是北京人,所以已经够甜了。
有多少人挣扎着挤破头颅想要留在这个城市,二十年后他的孩子才会吃着甜甜的糖霜山楂,扫着四合院里的雪长大。
我咬着糖霜山楂的纸袋子把小黄车停在宿舍楼下,在上楼的时候长舒一口气,然后开始想象一个很长的故事。
我想象大漠孤月,长烟直上,想象有人站在高楼的尽头,穹顶下燃起一把滔天的大火;我想象一个久久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,想象人世间所有震动胸膛的猎猎回响。
我贪婪地妄图以文字描摹一个永不结束的故事。我饿着肚子写下一行又一行字,然后把一个又一个糖霜山楂放进嘴里。
那一年我的确写完了一个故事。
这么多年来我艰难地尝试过很多东西。我十五岁的某个下午挨了老师一顿臭骂,于是丢下满屋子叮叮当当的试管,蹲在实验室的走廊上给教了我两年的师兄打电话,他大二的时候告诉我他喜欢上一个师姐,但念到博士他仍然孤身一人。很多年后他背着行囊从很远的地方回来,我们一起坐在家里刚好能容纳两个废人的沙发上看动画片,好像我十五岁的时候躲着班主任偷偷溜去实验室找放暑假回来的他。
六年之后的他胡子拉碴恰似一个博士应有的面貌,画面里圆滚滚的小姑娘踮起脚寄信给远方的老友。他问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同他在电话里哭,说不想去北京上大学吗。我愣了一会,想了三圈。我说忘了。
我又说,我好累啊,我不想再学编程了。
说到这里我好像隐约记起了什么。“我不想学这个了。” 兴许当年,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。
这世间真正坚强不屈的人太少了,对普通人而言前三步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。好像做过一些事,像蜗牛一样缓慢地爬过了,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是路面上潮湿的痕迹。
唯一贯穿全部的,只有静静留在笔尖下的文字。
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,一线喘息的少年时代,疲惫迷茫的青年时代。
我是一条被拍在岸上的鱼,挣扎着钻进不属于我的奇幻世界之后,才可以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。
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么一丁点人可以称成为作家,成为诗人,成为真正书写故事的人,有多少人终其一生也登不上巴比伦塔的第一层,但很长的一段时间,于我而言,它就是能用来逃避现实的整个世界。
我能做的只有写下去,继续写下去,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,长出一点点,小小的春天。